追溯“杰青情缘”:那些年,我们是杰青
2013-11-26 孙爱民 中国科学报
对于许多科研工作者来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杰青基金带来的不仅是科研资金,更是一个研究兴趣得以延续的平台。这个平台使他们获得了开拓学术领域的机遇以及完善科研版图的条件。1996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科院院士陈小明在做实验。有一群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成为研究领域内的佼佼者、学术带头人乃至两院院士;他们建立科研团队、开拓研究领域,荣获国家各类科技奖项,并且带着十足的底气和实力与国内外同行
对于许多科研工作者来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杰青基金带来的不仅是科研资金,更是一个研究兴趣得以延续的平台。这个平台使他们获得了开拓学术领域的机遇以及完善科研版图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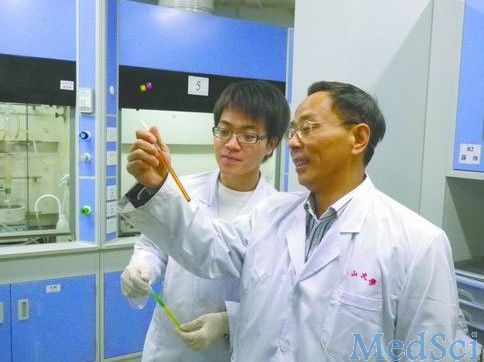
1996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科院院士陈小明在做实验。
有一群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成为研究领域内的佼佼者、学术带头人乃至两院院士;他们建立科研团队、开拓研究领域,荣获国家各类科技奖项,并且带着十足的底气和实力与国内外同行合作、竞争。
他们就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杰青基金”)获得者。
从1994年设立至今,杰青基金已经走过20年。20年,获得者们所取得的成绩成了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引才、育才、用才制度的最好注解。
“窥一斑而知全豹。”《中国科学报》记者追溯几位获得者的“杰青情缘”,试图从中发现杰青基金在人才成长中的独特作用。
“窥一斑而知全豹。”《中国科学报》记者追溯几位获得者的“杰青情缘”,试图从中发现杰青基金在人才成长中的独特作用。
杰青夫妻 拽我们打消顾虑回国
要不是杰青基金,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程和平与肖瑞平夫妇俩说不定还要在国外多漂几年。
1995年,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生理系博士毕业的程和平,在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老年研究所谋得一职。对细胞钙信号转导研究充满兴趣的程和平,在该所心血管科学实验室钙信号研究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顺利成为研究室主任、资深研究员。
尽管在国外硕果累累,程和平对回国却一直念念不忘。“我一直都想回来,但是实在舍不得花国家的钱:研究设备很贵,而且要从国外买,每一个设备都需要几个火车皮才能运回来。”程和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花国家这么多钱,顶多发几篇paper,so what?”
然而,国家对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的加大与杰青基金的设立,让程和平“开拓了思路”,同时也为他回国带来了转机。
1998年,程和平申请到杰青基金B类,开始了“一半时间在美国、一半时间在北大”的两头跑征途。
2002年,程和平彻底辞掉NIH高级研究员的终身职位,以“连根拔”的方式正式回国。
“是杰青基金把我‘拽’回来的。”在谈到那段经历时,程和平感慨万千。
刚回国时,程和平还是有一定心理落差的,但杰青基金的种种支持逐渐打消了他的顾虑,让他慢慢看到“科学在中国的土壤上一样能结出丰硕果实”。
“国内学生很可爱,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如果有一个学术能力强的人带领,他们可以作出很不错的成绩。”有了杰青基金的资助,程和平随后跟NIH的合作也变得“顺理成章、更有底气”。
“我最初的几篇论文都是在‘杰青’的支持下完成的。”程和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而肖瑞平几乎完全复制了丈夫程和平的经历。
2003年,辞掉NIH“金饭碗”的肖瑞平,踏着丈夫的足印回到北大工作。此前在NIH,她每年的研究经费有近100万美元,此外,她还获得了150万美元的外拨经费。
在肖瑞平看来,放弃优越的科研环境和安逸的生活,源于“灵魂深处永远都是中国人”与“更深的归属感和成就感”,而后者的源泉则是她2002年获得的杰青基金。
“杰青项目的进展让我觉得在国内可能会更有作为,人生也会更有意义。”如今已是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的肖瑞平如是说。
在程和平看来,在国内杰青基金仍然是目前含金量最高的科研资助项目,“经费不一定最高,但水准是最高的,它是青年科学家从事科学的标杆”。
“杰青不太在乎你做什么,能不能够做出来,它更看重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投资。”回国十多年,重新审视这项制度,程和平觉得“从长远来看,作为人才基金,杰青基金对科研的促进作用会比普通项目基金大得多”。
杰青师徒 容我们自由大胆尝试
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生陈小明回到他的母校中山大学任教。他任教的无机化学专业当时在中山大学不是重点学科,也没有重点实验室。
“当时学校的研究条件很差,我本人既没有仪器、研究经费,也没有相关基础,是一个‘三无人员’。”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中山大学生物无机与合成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的陈小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调侃自己。
1993年,陈小明申请到第一笔金额为5万元的青年基金项目,再加上学校与导师的扶持,他的科研工作得以维持。
1996年,青年基金项目结题后,因为后续科研经费的问题,陈小明一度被是否继续从事自己所钟爱的金属酶模型化合物与金属簇合物研究所困扰。但随后到来的国家杰青基金让他短暂的迷茫与恐慌烟消云散。
“太高兴了,那时候特别缺钱,四年80万元,绝对是雪中送炭。”陈小明告诉记者,最大的变化是招生与建立队伍变得不再困难。“在那个年代,无机化学招生很困难,招到的通常都是调剂过来的学生。”
获得资助当年,孤军奋战多年的陈小明开始招收博士生。由此,他很快建立起自己的课题组。研究团队的组建使得研究工作变得顺畅起来,陈小明的团队当年便有了成果,刊发了学科内影响因子最高的论文,并获得1996年的中国青年科技奖。
“只能拼了,豁出去好好干。”拿到杰青基金,陈小明在高兴之余,感受最多的则是压力与责任感, “做不好就对不起国家的培养,而这种激励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也促使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很晚,通宵工作成为家常便饭。
这种工作状态也激励着陈小明身边的人。慢慢地,他发现,同事中获得杰青基金的其他几个人也像他一样斗志昂扬,几乎全都扎根在实验室里。
“杰青基金似乎有一种魔力,一旦得到它,你的研究工作就有了动力。”陈小明如是说。
同样的感受也体现在陈小明的学生、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龙腊生身上。龙腊生是陈小明获得杰青基金的5名学生中的一位。
同导师一样,龙腊生刚到厦门大学开始研究工作时,学校的学科建设并不强,而在中山大学的科研经历为龙腊生在新环境中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1999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的龙腊生,到厦大先做了3年教学工作,之后才重拾科研,最初的几年,龙腊生备受压力“折磨”。
龙腊生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有机复合材料合成,而这个方向是一个长线的研究方向,需要长期、持续的经费支持。
“面上项目每年都要申请,可当时的资助强度比较小,一般三年35万元,只能‘小打小闹’。”作为一名“青椒”的龙腊生,不得不将时间与精力转向其他更容易出文章的领域。
2008年,龙腊生顺利申请到杰青基金,“我顿时感觉到这个研究方向有了希望。”200万元的项目资金,龙腊生第一年就拿到了120万元的启动经费,他还得到学校100万元的资助,而所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也获得了相应的配套。
“从那以后,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地从事科研,不用每年都急着发文章、完成任务,而是更注重长线科研的重要性。”龙腊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杰青基金最好的地方在于容许失败。”在谈到与其他资助项目的不同时,龙腊生表示,“基础研究对前沿方向的探索有风险和各种可能性,杰青基金恰恰遵循了科学研究的这一规律。”
导师陈小明亦有同感:“在研究进行中间,如果发现有其他更好的方向和想法,都可以去尝试。这对青年科研工作者尤其重要。杰青基金更注重创新性,而不仅限于可行性。”
现在的陈小明常以专家评委的身份出现在中青年科学家群体面前,因此他对如何鼓励青年人科研创新有着更深的体会。“容许你自由探索,让你的科学研究成体系、成板块地构建,这对科学的发展太重要了。”
杰青馆长 助我们补齐研究网络
“自由探索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乔格侠研究员以这样一句感慨,开启了她关于杰青基金的话题。
作为一名中科院的科学家,按照国家的需求申请课题、定位研究方向已成为乔格侠的固定思维,而她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往往无暇顾及。
从2005年开始,乔格侠便对DNA条形码相关的工作产生兴趣,带着学生开展有关研究。
自从加拿大科学家Paul Hebert于2003年提出这一概念后,DNA条形码已成为生物学领域发展最迅速的学科前沿之一。这一利用标准基因片段对物种进行快速和准确鉴定的新技术,早就进入了乔格侠的视野。
然而“固定思维”限制了对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一直都没有特别好的项目来支持。”正当乔格侠为此苦恼的时候,2010年杰青基金的出现为她带来了一盏明灯。
有了杰青基金的支持,乔格侠开始“撒了欢”地进行DNA条形码相关的探索。如今,她带领团队在DNA条形码新标记的筛选、新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均取得了突破,至今已发表五六篇高水平文章。
不仅如此,基于DNA条形码的研究成果,乔格侠又承担了科技部基础工作专项。“杰青的支持对于这个科技部大专项的完成必不可少。”乔格侠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以前的研究网络都是在进行应用研究的过程中搭建起来的,学术体系不够健全,缺少科学家自身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杰青基金帮我补齐了研究网络。”
乔格侠申报的杰青基金研究方向是昆虫系统学与分类。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研究领域,而乔格侠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多少限制,“基金委不给任何的压力与提示”。
这种开放与充分保证研究空间的项目导向,也让乔格侠在培养学生方面改变了以往拘谨的一面。“以前培养学生总有一些拘谨,我会让他们按照任务要求来做,偏离任务目标,就要往回拽一拽。现在我会让学生站在学科前沿跟我一起自由探索。”
对于乔格侠而言,目前国内林林总总的人才计划,多以吸引国外人才为主,对国内一批高水准人才关注不够,而杰青基金恰恰给了这些人才成长的空间。
明年,乔格侠的杰青基金项目就要结题。在杰青基金护航之下开展科研工作的乔格侠信心满满,“能够自由探索的科学家是最幸福的!”
杰青心声 让我们寄望基金未来
“品牌”、“荣誉”、“平台”、“口碑”,这是科学家评价杰青基金常用的词汇,而谈到未来发展,“灵活”一词也频频出现在他们的口中。
前不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到中山大学调研,陈小明在座谈期间曾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表示:“杰青基金现在已经有了品牌效应,未来发展要进一步强化这种效应,挑战自己。” 陈小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杰青基金应该更加灵活,盘子应该再大一些。“目前杰青基金200万元的资助金额有点偏少,除去物价因素,整个国家与社会对研究成果、研究水平的要求更高了。”
龙腊生则认为杰青基金在资金方面应该更加“灵活”。
“科学研究并不是说项目一结题就结束了,一个好的研究方向值得倾其一生去探索。”龙腊生建议杰青基金可以尝试给优秀答辩人追加一部分延续研究的资金,“这样不仅能起到激励作用,还能延续之前的研究方向与成果”。
而乔格侠关注的是杰青基金在年龄限制方面的灵活性。
“目前45岁的门槛是20年前制定的,现在科学家群体的状况及我国的科学环境与当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应该作出一些相应调整。”乔格侠为此建议不妨参考青年基金项目对于年龄限制方面的调整。目前,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对女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为40岁以下,男性为35岁以下。
程和平则对杰青基金经费管理与分配的灵活性充满期待。
“杰青基金现在要想超越自己,在科学方面必须更大胆一些,经费的管理与分配应更加灵活。”程和平直言,到了杰青这个层次的科技工作者,出成果已经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成果的创新性。
1995年,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生理系博士毕业的程和平,在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老年研究所谋得一职。对细胞钙信号转导研究充满兴趣的程和平,在该所心血管科学实验室钙信号研究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顺利成为研究室主任、资深研究员。
尽管在国外硕果累累,程和平对回国却一直念念不忘。“我一直都想回来,但是实在舍不得花国家的钱:研究设备很贵,而且要从国外买,每一个设备都需要几个火车皮才能运回来。”程和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花国家这么多钱,顶多发几篇paper,so what?”
然而,国家对基础研究支持力度的加大与杰青基金的设立,让程和平“开拓了思路”,同时也为他回国带来了转机。
1998年,程和平申请到杰青基金B类,开始了“一半时间在美国、一半时间在北大”的两头跑征途。
2002年,程和平彻底辞掉NIH高级研究员的终身职位,以“连根拔”的方式正式回国。
“是杰青基金把我‘拽’回来的。”在谈到那段经历时,程和平感慨万千。
刚回国时,程和平还是有一定心理落差的,但杰青基金的种种支持逐渐打消了他的顾虑,让他慢慢看到“科学在中国的土壤上一样能结出丰硕果实”。
“国内学生很可爱,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如果有一个学术能力强的人带领,他们可以作出很不错的成绩。”有了杰青基金的资助,程和平随后跟NIH的合作也变得“顺理成章、更有底气”。
“我最初的几篇论文都是在‘杰青’的支持下完成的。”程和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而肖瑞平几乎完全复制了丈夫程和平的经历。
2003年,辞掉NIH“金饭碗”的肖瑞平,踏着丈夫的足印回到北大工作。此前在NIH,她每年的研究经费有近100万美元,此外,她还获得了150万美元的外拨经费。
在肖瑞平看来,放弃优越的科研环境和安逸的生活,源于“灵魂深处永远都是中国人”与“更深的归属感和成就感”,而后者的源泉则是她2002年获得的杰青基金。
“杰青项目的进展让我觉得在国内可能会更有作为,人生也会更有意义。”如今已是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的肖瑞平如是说。
在程和平看来,在国内杰青基金仍然是目前含金量最高的科研资助项目,“经费不一定最高,但水准是最高的,它是青年科学家从事科学的标杆”。
“杰青不太在乎你做什么,能不能够做出来,它更看重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投资。”回国十多年,重新审视这项制度,程和平觉得“从长远来看,作为人才基金,杰青基金对科研的促进作用会比普通项目基金大得多”。
杰青师徒 容我们自由大胆尝试
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生陈小明回到他的母校中山大学任教。他任教的无机化学专业当时在中山大学不是重点学科,也没有重点实验室。
“当时学校的研究条件很差,我本人既没有仪器、研究经费,也没有相关基础,是一个‘三无人员’。”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中山大学生物无机与合成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的陈小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调侃自己。
1993年,陈小明申请到第一笔金额为5万元的青年基金项目,再加上学校与导师的扶持,他的科研工作得以维持。
1996年,青年基金项目结题后,因为后续科研经费的问题,陈小明一度被是否继续从事自己所钟爱的金属酶模型化合物与金属簇合物研究所困扰。但随后到来的国家杰青基金让他短暂的迷茫与恐慌烟消云散。
“太高兴了,那时候特别缺钱,四年80万元,绝对是雪中送炭。”陈小明告诉记者,最大的变化是招生与建立队伍变得不再困难。“在那个年代,无机化学招生很困难,招到的通常都是调剂过来的学生。”
获得资助当年,孤军奋战多年的陈小明开始招收博士生。由此,他很快建立起自己的课题组。研究团队的组建使得研究工作变得顺畅起来,陈小明的团队当年便有了成果,刊发了学科内影响因子最高的论文,并获得1996年的中国青年科技奖。
“只能拼了,豁出去好好干。”拿到杰青基金,陈小明在高兴之余,感受最多的则是压力与责任感, “做不好就对不起国家的培养,而这种激励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也促使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很晚,通宵工作成为家常便饭。
这种工作状态也激励着陈小明身边的人。慢慢地,他发现,同事中获得杰青基金的其他几个人也像他一样斗志昂扬,几乎全都扎根在实验室里。
“杰青基金似乎有一种魔力,一旦得到它,你的研究工作就有了动力。”陈小明如是说。
同样的感受也体现在陈小明的学生、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龙腊生身上。龙腊生是陈小明获得杰青基金的5名学生中的一位。
同导师一样,龙腊生刚到厦门大学开始研究工作时,学校的学科建设并不强,而在中山大学的科研经历为龙腊生在新环境中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1999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的龙腊生,到厦大先做了3年教学工作,之后才重拾科研,最初的几年,龙腊生备受压力“折磨”。
龙腊生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有机复合材料合成,而这个方向是一个长线的研究方向,需要长期、持续的经费支持。
“面上项目每年都要申请,可当时的资助强度比较小,一般三年35万元,只能‘小打小闹’。”作为一名“青椒”的龙腊生,不得不将时间与精力转向其他更容易出文章的领域。
2008年,龙腊生顺利申请到杰青基金,“我顿时感觉到这个研究方向有了希望。”200万元的项目资金,龙腊生第一年就拿到了120万元的启动经费,他还得到学校100万元的资助,而所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也获得了相应的配套。
“从那以后,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地从事科研,不用每年都急着发文章、完成任务,而是更注重长线科研的重要性。”龙腊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杰青基金最好的地方在于容许失败。”在谈到与其他资助项目的不同时,龙腊生表示,“基础研究对前沿方向的探索有风险和各种可能性,杰青基金恰恰遵循了科学研究的这一规律。”
导师陈小明亦有同感:“在研究进行中间,如果发现有其他更好的方向和想法,都可以去尝试。这对青年科研工作者尤其重要。杰青基金更注重创新性,而不仅限于可行性。”
现在的陈小明常以专家评委的身份出现在中青年科学家群体面前,因此他对如何鼓励青年人科研创新有着更深的体会。“容许你自由探索,让你的科学研究成体系、成板块地构建,这对科学的发展太重要了。”
杰青馆长 助我们补齐研究网络
“自由探索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乔格侠研究员以这样一句感慨,开启了她关于杰青基金的话题。
作为一名中科院的科学家,按照国家的需求申请课题、定位研究方向已成为乔格侠的固定思维,而她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往往无暇顾及。
从2005年开始,乔格侠便对DNA条形码相关的工作产生兴趣,带着学生开展有关研究。
自从加拿大科学家Paul Hebert于2003年提出这一概念后,DNA条形码已成为生物学领域发展最迅速的学科前沿之一。这一利用标准基因片段对物种进行快速和准确鉴定的新技术,早就进入了乔格侠的视野。
然而“固定思维”限制了对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一直都没有特别好的项目来支持。”正当乔格侠为此苦恼的时候,2010年杰青基金的出现为她带来了一盏明灯。
有了杰青基金的支持,乔格侠开始“撒了欢”地进行DNA条形码相关的探索。如今,她带领团队在DNA条形码新标记的筛选、新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均取得了突破,至今已发表五六篇高水平文章。
不仅如此,基于DNA条形码的研究成果,乔格侠又承担了科技部基础工作专项。“杰青的支持对于这个科技部大专项的完成必不可少。”乔格侠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以前的研究网络都是在进行应用研究的过程中搭建起来的,学术体系不够健全,缺少科学家自身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杰青基金帮我补齐了研究网络。”
乔格侠申报的杰青基金研究方向是昆虫系统学与分类。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研究领域,而乔格侠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多少限制,“基金委不给任何的压力与提示”。
这种开放与充分保证研究空间的项目导向,也让乔格侠在培养学生方面改变了以往拘谨的一面。“以前培养学生总有一些拘谨,我会让他们按照任务要求来做,偏离任务目标,就要往回拽一拽。现在我会让学生站在学科前沿跟我一起自由探索。”
对于乔格侠而言,目前国内林林总总的人才计划,多以吸引国外人才为主,对国内一批高水准人才关注不够,而杰青基金恰恰给了这些人才成长的空间。
明年,乔格侠的杰青基金项目就要结题。在杰青基金护航之下开展科研工作的乔格侠信心满满,“能够自由探索的科学家是最幸福的!”
杰青心声 让我们寄望基金未来
“品牌”、“荣誉”、“平台”、“口碑”,这是科学家评价杰青基金常用的词汇,而谈到未来发展,“灵活”一词也频频出现在他们的口中。
前不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到中山大学调研,陈小明在座谈期间曾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表示:“杰青基金现在已经有了品牌效应,未来发展要进一步强化这种效应,挑战自己。” 陈小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杰青基金应该更加灵活,盘子应该再大一些。“目前杰青基金200万元的资助金额有点偏少,除去物价因素,整个国家与社会对研究成果、研究水平的要求更高了。”
龙腊生则认为杰青基金在资金方面应该更加“灵活”。
“科学研究并不是说项目一结题就结束了,一个好的研究方向值得倾其一生去探索。”龙腊生建议杰青基金可以尝试给优秀答辩人追加一部分延续研究的资金,“这样不仅能起到激励作用,还能延续之前的研究方向与成果”。
而乔格侠关注的是杰青基金在年龄限制方面的灵活性。
“目前45岁的门槛是20年前制定的,现在科学家群体的状况及我国的科学环境与当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应该作出一些相应调整。”乔格侠为此建议不妨参考青年基金项目对于年龄限制方面的调整。目前,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对女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为40岁以下,男性为35岁以下。
程和平则对杰青基金经费管理与分配的灵活性充满期待。
“杰青基金现在要想超越自己,在科学方面必须更大胆一些,经费的管理与分配应更加灵活。”程和平直言,到了杰青这个层次的科技工作者,出成果已经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成果的创新性。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内容来源注明为“梅斯医学”或“MedSci原创”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梅斯医学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为“梅斯医学”。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或“梅斯号”自媒体发布的文章,仅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站仅负责审核内容合规,其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不负责内容的准确性和版权。如果存在侵权、或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在此留言
本网站所有内容来源注明为“梅斯医学”或“MedSci原创”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梅斯医学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为“梅斯医学”。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或“梅斯号”自媒体发布的文章,仅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站仅负责审核内容合规,其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不负责内容的准确性和版权。如果存在侵权、或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在此留言








#杰青#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