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How Doctors Think——如何面对医疗实践中的不确定性?
2015-05-08 昆仑霞 医学生
1、从一篇很火的帖子说起 一篇名为 “杨娃娃腰椎穿刺惊魂夜”的帖子在微博和论坛遭到热议。 故事的大意是:作者年幼的女儿突然开始发烧,吃了退烧药仍然烧到38度多,于是到中日友好医院化验,结果白血球稍高。医生认为嗓子炎症,开了抗生素。 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多,娃娃烧到39度多,直送到儿童医院。由于普通急诊前面排了50多个孩子,等半个小时只看了3个,于是换成200块钱的夜间特需专家急诊,无需排队。
1、从一篇很火的帖子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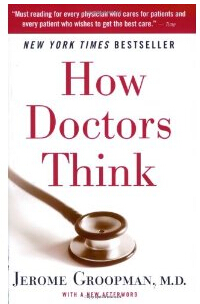
故事的大意是:作者年幼的女儿突然开始发烧,吃了退烧药仍然烧到38度多,于是到中日友好医院化验,结果白血球稍高。医生认为嗓子炎症,开了抗生素。
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多,娃娃烧到39度多,直送到儿童医院。由于普通急诊前面排了50多个孩子,等半个小时只看了3个,于是换成200块钱的夜间特需专家急诊,无需排队。
特需急诊医生常规检查后,开始把娃娃放在病床上,头反复抬起放下,腿反复弯曲拉开。这时家长开始紧张起来,疑涉及神经系统,做过几次后,医生怀疑是急性脑膜炎,建议做腰椎穿刺。反复问除了做腰穿外有无其他诊断方法,答说没有。
作者心理开始纠结:腰穿非常痛苦,孩子无法承受;且有一定风险,可能伤到神经,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不做,脑膜炎可能造成脑损伤以及其他更可怕的后遗症。最后还是决定做。
但抢救室的大夫拒绝做腰穿,因为没有签家属确认书。
回到专家处,专家称他觉得应该在抢救室签,经作者要求后,找半天找不到腰穿确认书在哪里。最后终于找到。
签了确认书,抢救室的大夫仍然拒绝做腰穿,要求必须先做脑CT。
作者绝望中拨打了一位认识的协和医院医生电话,经建议前往协和医院门诊。医生做了一系列检查之后,判定孩子就是感冒发烧,不必做腰穿和CT。作者询问关于儿童医院要做腰穿的事情后,医生解释说她已经在检查前仔细看了儿童医院的诊断记录,结合对患儿情况的询问结果,确认不是脑炎,并向作者详细解释了原因。孩子最终无事,一家人总算是放心了。
此文一出,立刻遭到疯传和热议。大多数评论把矛头指向了儿童医院的专家和门诊体制。其中不乏谩骂和抱怨。通过这篇文章的反应,不难看出现在我们对于医生的担忧与怀疑。但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医生的道德,真的已经败坏了吗?一个穿刺几十块钱,医生放着好好的觉不睡,会为了这几十块钱冒着风险给孩子做穿刺?(实际上发给医生的可能只有几块钱),儿童医院医生要做穿刺的动机在哪里?
一本叫做 How Doctors Think 给了我们答案。
2、 “好医生”与“坏医生”
首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Jerome Groopman,医学博士,哈佛医学院教授,波士顿Beth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的医学实验主任。Groopman博士是放射学和癌症治疗方面的专家,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他还是《纽约客》的撰稿人。为了写这本关于医生在临床中的行为决策过程及失误分析的书,他采访了很多临床医师,用他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就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向我们展示了医生在为患者进行诊断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为什么他们有的时候,会不可避免的犯错。其中有一些内容是颠覆了我们的认识的,比如,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好医生”有时反而会害了病人。
布拉德·米勒是非常阳光可爱的一个小男孩,热爱跑步。他因为腿部的骨肉瘤而住院,但却仍然热切地渴望着回到跑道上去。作者非常喜欢这个小男孩,非常认真地为他治疗。为了防止截肢,米勒需要经历非常痛苦的化疗。一次化疗后,作者在巡诊时为他进行例行检查,化疗严重伤害了他的免疫系统,医生需要确定他没有感染的危险。但在两个人愉快交谈后,他认真地检查了男孩身上的大部分,没有任何异常。
“今天就到这里。”作者希望这个可怜可爱的孩子好好地休息一下。
但在当天晚些时候,一名住院医师紧急通知他“布拉德·米勒没有了血压”。男孩开始发高烧,并被送往ICU,对于他这种免疫系统几乎失效的病例来说,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死亡。
作者询问情况后发现,感染源来自于男孩臀部的一个脓肿。他马上想起,当时虽然检查了他身上大部分地方,但是只有臀部和直肠没有检查。因为这需要翻过身来,而他潜意识里并不忍心看到一个虚弱、疲惫,但仍对生活充满乐观和期许的少年承受更多的痛苦了,他只希望让男孩早点休息。
作者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感到十分悔恨,尤其是他在赶到ICU之后,看到男孩还在抬起手来向他打招呼时,他感到更加痛苦。所幸,最后男孩幸存了下来。但是作者明白了,有的时候,医生对人的好意,却可以蒙蔽他们理性的判断力,最终害了患者。
3、代表性错误
医生也是人,人都会受到思维误区的影响。Groopman博士在本书中指出的第一个误区叫做representative error(代表性错误)。
当一名40岁出头,身材健壮、肤色健康、头发浓密,看上去就像那些古希腊雕塑一样的护林员因为突然的胸部疼痛而去看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时,这位医生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还是详细地询问了疼痛的病史和情况,并对患者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并没有大的异常,这位护林员的生活方式非常健康,家族也没有心脏病史。此外,医生一直在认真按照“心脏及肺部疾病风险因素表”逐一核实,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于是便告诉护林员:这可能是某些肌肉过度使用造成的疼痛,他的心脏病风险几乎为0。
第二天,这名医生歇班。当他晚上出去跑步路经医院急诊室前面时,碰到了自己的一名同事。同事见到他就说:“你昨天看的那个人,今天早上因为严重的心肌梗死住院了。”
医生大吃一惊,他回到医院,反复查看昨日的诊疗记录。他的同事安慰他说:“如果当时是我看的这个人,我甚至都不会像你那样对他进行全套的检查。”但是,医生听了这话却并不觉得安慰。这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自己从不会犯错,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非常普遍的认知错误:当他第一眼看到这个病人,就把他当作了一个“健康中年男子”的典型,而这个典型形象在他的潜意识里挥之不去,对他的判断产生了影响。他是一个经验如此丰富的医生,并且严格照章办事,非常认真地为护林员进行了每一项检查。即便如此,头脑中最先形成的既成印象“这是一个健康的家伙”却仍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的重大失误。
4、可获得性启发
Groopman博士指出,医生常犯的另一个重要误区叫做“可获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它指在很多时候,人们只是简单根据他们对事件已有的信息,包括记忆的难易程度或记忆中的多寡,来确定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寻找去其他相关的信息,容易被知觉到或回想起的被认为更容易出现。事件刺激的频率、新异性、生动性、情绪性也会影响到其可获得程度,从而影响到其在个体心目中的主观概率。诺奖得主Kahnemann 和他的同事 Tversky 研究了根据想起一个例子的速度来评价某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问题,发现这种方法存在严重的回忆偏向和搜索偏向,因为人们在记忆中搜寻相关信息时,并不是所有的相关信息都能被无偏差地搜索到。
比如说上面这位医生,当他经历了如此重大的失误之后,他在以后一段时间的诊疗中,对于看似健康的人的各种症状会更加加以注意,这反而增加了他做出“伪阳性”诊断——把本来没有心肌梗死风险的人诊断为心肌梗死,或者夸大它发生的风险——的可能性。
5、锚定效应
一家收留了众多酒精依赖症患者的医院,他们多数会在戒酒之后出现戒断症状——震颤性谵妄(DT),表现为不可控制的发抖。当一位医生在接待了十名DT患者后,他极有可能在简单诊断之后就确定第十一名出现不可控发抖症状的人患有DT,但实际上有一长串疾病都有可能造成相同症状。
上述案例的诊断过程叫做“锚定效应(anchoreffect)”的心理现象有关。它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数值作为起始值,起始值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在做决策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给予最初获得的信息过多的重视。《吕氏春秋》中讲过一个故事:“人有忘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这个丢斧子的人心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时,一切指向模糊的证据(甚至可能与假设是根本无关的),只要不能从正面完全证伪先入假设,都有可能被解释为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从而更加强化对先入假设的信心。
6、对杨娃娃案例的反思
现在我们来回过头来思索一下开头的例子:是否是儿童医院的医生与协和医院医生所处的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他们之间诊断的差异?显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7、不可避免的思维误区
注意:这种误区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当一名工作负担沉重的医生需要在二十分钟、十分钟甚至更短时间内就必须做出诊断的情况下。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很多医师都主张诊断时要慎重,应该认真聆听病人的叙述,通过有效的提问引导病人提供有用信息,结合检查结果,列出所有的可能性。而在很多情况下,短期内无法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应该在和病人商谈的基础上,权衡风险效用比,采取试探性治疗,视情况随时改变治疗措施。这是一种基于理性的风险管理策略而发展出的方法,它的应用基础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但注意到在医疗实践中,很多情况下主客观条件都不允许这种反复试错的方法,医生必须依靠直觉而非按部就班的逻辑推理做出决策,这就使得思维误区变得几乎不可避免,也大大增加了诊疗的不确定性。
8、如何与不确定性相处?
为了写这本书,作者对大量的一线医生进行了访谈,其中不乏一些世界顶级的专家。他们都有着丰富的经验,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并且拥有美国全球顶尖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即便如此,他们却仍然在犯一些看似并不那么高级的错误。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并没有对这些错误提出谴责,而是详细地分析了错误的原因。首先,这些医生可能属于世界上最好的那一个级别,他们的医德也都很高,所以他们犯的错误就非常具有代表性意义:“如果一个医生水平很高,而且他也尽心为你治疗,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失败——即使是非常简单的病,那我们该怎么办?”
美国教育普遍非常重视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一种基于逻辑的、通过理性而开放的思考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教育渗透了美国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这些优秀的医生也不例外。而且,他们不但在技术上非常精湛,还拥有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工具,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误判。比如前面提到的“诊断表”,就是把某一病症相关的所有症状因素都列成一个清单,以供医生对照着逐一排查。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医生使用的国际评分系统,可以有效地帮助医生进行决策。美国的医生甚至掌握了贝叶斯(Bayesian)方法——一种计算概率的主要方法之一,这种应用数学工具可以帮助医生在面对多种可能的情况时,推算出每一种情况可能发生的概率。
但即使在如此完备的思维工具武装下,不确定性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作者在这本书中介绍了一个名叫洛克的医生。他是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心脏科主任,因为发明过多种心脏器材而享有知名度。洛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逻辑思维实践者,擅长使用推理的方法解决医疗中遇到的问题。但是他同时也承认,在一些时候,光靠逻辑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他多年行医生涯中经历的一些艰难的失败告诉他的。诚然,他使用的逻辑工具是无懈可击的,可是为什么逻辑会失败呢?问题就在于,每一个逻辑的推理都会有一个起点,而如果这个起点是错的,那么正确的逻辑只能忠实地把我们引导至错误的结论。为什么起点会错?洛克医生的解释是:“因为我的推理起点是一个没有任何过往经验可供参考的命题,所以我无法把所有变量纳入考虑之中——除非我实际去做了才能发现它们。这样,你只能做出错误的建议,然后你没能保住病人的生命。”
此外,洛克医生还指出:“我并没有足够地去考虑一些非常小的效应。比如说,氧水平的微小波动,虽然可能只有1%、2%、3%……但是却可以是心脏出了大问题的讯号。”
洛克医生的这番话值得我们去思索:考虑到医疗现场的现状,注意到这样的微小变化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比如医学影像技术,过去做X光片,正面一张侧面一张足矣;后来出现的CT技术使得一个病人几十张片子成了家常便饭,MRI则又把这个数量提升到了几百张,要看的片子增多了,病人却没有减少,这就使得医生的工作量大大增加。用作者的话说,医生就像是马戏团“转盘子的演员”一样,手里有很多盘子,哪一个也不敢怠慢。
但这并不是不敢怠慢的问题。在被数据和病患淹没的环境下,医生必然无法对每个现象都平等对待。所以他们会借助贝叶斯等方法,评估概率,把注意力集中在高概率事件上,抓大放小。这是一个合理的方法,也许是整体上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在工作中常常强调要事第一,医生的工作也是这样做的。但问题就在于医生每天处理的都是鲜活的生命,一些小概率的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可能就是病人的死亡,在中国,也许这还会伴随着家属的抱怨和诉讼。所以我们在精神上尚没有做好接受医生犯错的准备,这样的后果会对医生造成了严重的心理负担,他们会本能地采取明哲保身的方法,尽量避免做出铤而走险的决定。杨娃娃案例中的腰穿医师大概就是这样的例子。
不确定性,大概是医学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都不可避免的。书中将其原因归结为三个因素:第一,没有人能够掌握所有的医学知识。外科医生专看外科,心脏科专看心脏,它们之间的交集部分将会成为灰色地带。第二,现有的医学知识本身也是有局限的。第三个原因源自前两个:我们往往无法分清是个人知识或能力的局限,还是医学知识本身的局限。
但是,我们从思维构造上就不擅长于应对不确定性,医生也不例外。复杂的医疗现场的情况更是加剧了这种劣势。比如每个人的生理条件都是不一样的,一样的血糖值,有的人可能就会因高血糖而受到伤害,而有的人则可能安然无恙。同样的不良生活习惯,有的人可能很快就会受到惩罚,有的人可能一生安然无恙。虽然在医疗现场中有很多量化的评分标准,比如日本政府就规定了高血糖的参考值等。但医学并非一个可以精确量化的领域。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情况,在一个人身上有效的疗法可能在另一个人身上就会造成灾难,这也是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之一。但是,我们的医生却没有很好的办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首先是客观上的,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列出一个全面的分析方案,像福尔摩斯捉犯人一样细致入微地观察和推理出病源。他们往往只能按照“流程”,在有限时间内作出判断。而主观上的一些条件则加剧了这样的情况,除了给病人治病之外,他们需要考虑太多的其他因素:如果判断失败,是不是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使自己处于不利?如果我坦率地承认不知道原因,不远万里慕名而来,挂了好几天号的病人会不会觉得失望而愤怒?虽然这种病很快就会自愈,但病人家属坚持要开药,到底给不给他开?
而我们作为病患,或者家属,在对于医生面临的这种不确定性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往往也会陷入慌乱之中。关于杨娃娃的事情,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人抱怨道:“现在这种社会,看来我们都得掌握医学知识才能自保了”。掌握一定的医学常识自是必要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把钱直接交给基金经理而任其处置,自然也不应该把自己直接交给医生而言听计从。
不过,似乎我们都希望医生能够明确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前听一个朋友说,她检查出了一个潜在的病症,问医生应该如何处理。医生说这个可以治,也可以不治,它的风险就像过马路一样,你可能安全过马路一辈子,也有可能被车撞。朋友对这个答案大为不满。不过我倒是认为这个医生是个负责任的好医生,也许他打比方的能力还需要提高……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之间没有一个明确而合理的合作方式。普通人对医生的看法,基本上是“你就是一个物理学中的‘黑箱’,我不管你是什么结构,只要从左边输入进去,右边就要给我出来结果。我付了钱,不是来听你说你不知道,或者让你问我该怎么办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个确定的结果,如果我们认为医生“应该”可以解决某个问题,但他却没能解决,或者犯了错误,我们就会“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度”这个医生。而医生则受制于这种现实,以及各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关系,他行医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再可能是单纯的“治病救人”,而是变成了“明哲保身”、“利益最大化”。我不认为这是医生的错,因为冒着生命危险而采取激进方法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大多数思维正常的人都做不出来的,这个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这是各种综合因素导致的。病人不理解医生,医生有太多顾虑,双方由“合作”的关系变成了博弈的对立面,最终只能形成一种畸形的局面。
关于应对不确定性,本书的作者提供了一些解决的建议。比如患者可以积极地去问医生一些问题:“它还有什么可能?”、“有没有其他可以解释我的症状的原因?”“在我的病史、检查和实验室结果里有没有其他可能与我的症状相联系的情况?”,这些诚恳的问题可以帮助医生减少出现思维误区的风险。当然,作者所观察到的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医生,对我们来说,这几乎是“理想条件”,而我们则会遇到比这现实得多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询问“风险”做起。“这病如果治疗有什么风险?不治疗有什么风险?有没有其他选项?”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鼓励医生大胆地采取激进方法为自己治疗,而不必担心后果。而这样的判断,完全基于一个简单的“风险-收益”的思路,也就是说,我们的风险厌恶程度。
诚恳地和医生进行交流也是一个必要的举措。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应当是一个“顾问”或者“信息提供者”,他会把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然后由你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判断。如果你觉得难以做出判断,那么原因很可能是1)你还不会,或不愿意处理不确定性,2)你得到的信息还不够。如果是1),你需要勇敢地对自己的人生作出决定,而不是交给别人掌握,2)的话,你需要继续向医生请教,直到你得到足够做出决策的信息为止。此外,就像本书作者指出的,第二意见(second opinion)也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的知识和认知角度毕竟有限,当我们对决策感到不安时,也许去看另一个医生是很好的选择。甚至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可以在看了足够的医生,对情况有了足够的认识之后再做决策。本书作者讲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他的右手手腕因为疼痛而对使用造成了严重障碍。他先后看了3个医生,其中包括该领域世界顶级的专家,每个人都提出了不同的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但他在遇到第4个医生之前,都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对这些医生的思维过程和诊疗根据存有疑问。第4个医生的诊疗方法和解决方案非常大胆,但却让作者认为他的确细致地考虑到了每一个方面,到这个时候,他认为已经得到关于自己的病情能得到的所有信息了,所以他可以做出决定了,他决定采纳第4个医生的方案。而这时距离他去问诊第一个医生已经过去数年了。
诚如前面所讲,现在的医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作者是放射科的专家,但对于自己的手,他和我们一样,也要以一个普通病人的身份去看病,并且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才做出决策。所以,这不是“我们必须学会医疗知识才能生存”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面对不确定性才能生存”的问题。
9、什么是错误?
最后,再看看开头文章的作者——“杨娃娃”的爸爸是如何面对医生的不确定性的吧。他在最后写道:
“我并不想指责和埋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位医生,因为我相信每个医生都是希望能帮到病人的,只是人类对自身躯体的认知永远都会存在局限性,常常无法以对错来简单判定我们做出的选择。我只能庆幸娃娃并没有得那么重的病,并且庆幸我们还是懂得一些医学知识的家长,若对腰穿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一针就给娃娃扎了,这个罪孩子就遭上了,得到的或许也只是一个相同的结果。”
在我看来,前面的一句话说的非常高尚、优雅而宽容。但问题是到了第二句话,他突然话锋一转,表示之前做腰穿的经历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我不得不指出作者在这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导:因为孩子最终不是脑膜炎而认为腰穿没有必要,完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虽然不清楚当时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儿童医院的医生也许是真的有做腰穿的理由,在那种情况下,腰穿或许是风险-效用比最佳的方案。《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塔勒布曾经说过:并不是在事实发生之后才确定一件事是不是错误,而是要根据截至那一时点之前的信息。杨娃娃的爸爸在前半段用理性大度的语言包装自己,让人们对其心生敬重,然后在后半段却将一个严重的谬误埋在了内容中,植入到读者头脑中,也许他在主观上并没有这样的意识,但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方式更容易让人加深对医生的误解,造成的结果更加恶劣。从结果上看,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诋毁。
本网站所有内容来源注明为“梅斯医学”或“MedSci原创”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梅斯医学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为“梅斯医学”。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或“梅斯号”自媒体发布的文章,仅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站仅负责审核内容合规,其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不负责内容的准确性和版权。如果存在侵权、或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在此留言













了解,
139
了解,
157
了解,
127
好好学习
155
#OCT#
60
好好活着才能造福更多病人——
186
好好活着才能造福更多病人——
108
#CTO#
52
好文章!
113
挺不错的
125